肿瘤与免疫,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理想情况下,每每肿瘤细胞来袭,免疫细胞会立马挂帅冲往一线,与其展开殊死搏斗,将其驱逐出境。但实际情况是,难免会出岔子,肿瘤得以在体内野蛮生长。
过去十年,各类免疫治疗涌现,针对抑制性免疫检查点蛋白的PD-1、PD-L1和CTLA-4的单抗(MAB),还有过继性T细胞治疗,特别是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让不少癌症节节败退。当前,人们寻找新型癌症免疫治疗的热情,有增无减。
此外,现有免疫治疗并不是对所有癌症患者均有效,且全身给药能引发全身毒性风险。免疫治疗在癌症治疗领域想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亟需继续创新。
为此,学者们提出了改进策略:瘤内注射免疫治疗和靶向免疫治疗。
一、免疫治疗静脉给药的局限性
免疫治疗全身性肠外给药,优点缺点并存。
优势包括:血清药代动力学可预测、所需设施简单,药物研发常使用该方法。
局限性包括:
a、大分子和细胞从血液循环进入实体肿瘤有难度,通常渗透性有限,或未能进入靶细胞。
b、此外,全身性给药通常带来全身毒性,导致无法使用最佳剂量,如IL-12和抗CTLA-4单抗伊匹单抗。
c、此外,系统内稳态可快速消除免疫治疗的促炎症和/或免疫刺激作用,从而限制其抗肿瘤活性。
二、让免疫治疗在肿瘤局部更具威力的策略
静脉给药免疫治疗带来的以上局限性,选择性提高可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的药物在肿瘤微环境(TME)中的生物利用度,就可迎刃而解。
可通过以下策略达到以上目的:
1、重复或连续直接肿瘤内给药免疫治疗
多数器官,可在图像引导下肿瘤内注射给药。药物首先弥散到注射区域,在局部达到非常高的初始组织浓度,然后逐渐进入到体循环中。这种逐渐吸收入血的方法,有药代动力学的优势,可使用更高剂量,耐受性更好。重要的是,肿瘤内给药,药物可直接进入肿瘤引流淋巴结,该淋巴结则是启动和维持抗肿瘤免疫应答的关键枢纽。类似地,局部给药可直接进入肿瘤组织内的三级淋巴结构。
瘤内注射促炎性物质,可助免疫细胞一臂之力,解决棘手的“冷肿瘤”问题。“热肿瘤”是指PD-L1表达水平高,且肿瘤内浸润免疫细胞和淋巴细胞(TILs)较多。这类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付起来得心应手。但有的肿瘤,肿瘤间质有大量免疫细胞,但其无法浸润肿瘤,或者间质中也不见免疫细胞的踪迹,属于寸草不生型,就是所谓的“冷肿瘤”。“冷肿瘤”经常能让免疫治疗吃闭门羹。瘤内注射促炎性物质后,将病灶(或多个病灶)转变为“原位癌疫苗”,潜在诱导多数或所有转移灶以及微转移灶对肿瘤抗原免疫应答。
2、靶向免疫治疗
全身给予药物或药物前体,通过各种生物靶向策略对其进行改造,让其选择性在肿瘤组织或引流淋巴组织中积聚,或只在肿瘤组织才活力满满。
a、可将免疫治疗药物嵌合到一些分子上,这些分子或只与恶性组织中的肿瘤细胞、基质细胞或细胞外基质有亲和力,或是亲和力更高。如此一来,即便全身给药,只有肿瘤组织才是药物的落脚之地,其他组织只是过路。
b、可借助运输工具,如基于脂质的微泡或纳米囊泡,将药物运送到肿瘤组织,再慢慢卸货,提高其在肿瘤内的生物利用度。
c、全身给予没有活性的前药,只有肿瘤组织才能赋予其活力。通常是利用了只有肿瘤组织才有的生物或物理化学特点,如低pH值、高浓度ATP或蛋白酶过度表达,达到只有肿瘤组织才能激活前药的目的。
d、将上一方法稍作变化,将有破坏力的病毒设计成只对肿瘤组织开炮,或者只在癌细胞中表达转录目标基因。例如,病毒可以携带多种免疫转录基因,如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FLT3配体、抗CTLA-4单抗或共刺激配体。
三、现阶段成果梳理
尽管存在新的挑战,肿瘤内注射和肿瘤组织靶向免疫治疗潜力巨大。随着许多临床研究的进行,目前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1、瘤内注射免疫疗法
(1)模式识别受体激动剂 放入“假的病原微生物”在肿瘤局部引发战争
固有免疫应答是机体抵御外来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该过程主要由人体内的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通过受体识别微生物特有的生物分子——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发现感染,这些受体称为模式识别受体(PRRs)。
人体内的的固有免疫PRR,主要包括Toll样受体家族(TLR)、细胞质RNA解旋酶RIG-I样受体(RGR)家族、环状GMP-AMP合成酶(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系统。
人体内的微生物防御体系已进化出哪有感染和/或组织损伤,就只在哪个局部抗争的能力,从而防止全面爆发战争,殃及无辜。
使用PRR激动剂进行瘤内免疫治疗,就是模拟了这一过程,让“假的微生物”(病毒或细菌)在肿瘤局部引起细胞毒性CD8+T细胞反应,并刺激CD4+T细胞产生IFNγ,诱导或增强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
1)TLR9激动剂
TLR9激动剂是由短的、连续未甲基化CpG寡核苷酸组成。细菌和病毒DNA中,常见的是未甲基化CpG寡核苷酸,但人体中受到抑制或甲基化。将未甲基化CpG寡核苷酸注射到肿瘤部位,可激活先天性免疫反应,使得“冷肿瘤”变成“热肿瘤”。目前,有的TLR9激动剂是单药治疗,有的联合了已有全身性免疫治疗。
瘤内注射TLR9激动剂CpG7909、SD-101,目前正在研究用于惰性淋巴瘤或蕈样肉芽肿。瘤内注射SD-101联合全身性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晚期黑色素瘤,初步显示有一定效果,且观察到T细胞肿瘤浸润增加的证据[1]。
tilsotolimod/IMO-2125联合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用于治疗PD-1抑制剂治疗失败的无法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的1/2期临床数据显示,22%的患者出现客观应答(ORR),71%的患者达到疾病控制,总生存期(OS)为21个月,表现耀眼[2]。
其它瘤内注射TLR9激动剂包括MGN1703和CMP101,正进行临床研究。
2)TLR7和TLR8激动剂
TLR7和TLR8是可识别病毒特征性单链RNAs(ssrna)的内涵体受体。TLR7和TLR8激动剂的抗肿瘤作用包括:增强自身免疫、增强T细胞免疫和诱导TLR阳性肿瘤细胞的凋亡。
咪唑喹啉家族化合物是TLR7和TLR8的受体激动剂,包括咪喹莫特和雷西莫特。
咪喹莫特乳膏制剂,局部用于治疗生殖器疣、浅表基底细胞癌病灶。此外,已开展咪喹莫特联合放疗用于乳腺癌皮肤转移的研究,可将放疗局部应答率从11%提高到66%[3]。
雷西莫特凝胶制剂,局部使用对皮肤T细胞淋巴瘤具有临床活性。
但是,肿瘤内注射TLR7/8激动剂,仍有待探索。
3)TLR4激动剂
TLR4是人体内一种可识别细菌脂多糖(LPS)的细胞表面受体,因其在脓毒性休克和浆状树突细胞成熟中的发挥作用而被发现。鉴于TLR4是脓毒性休克的主要介质,全身用药很危险,需要局部靶向。
TLR4激动剂G100是一种完全人工合成的LPS类似物。已在一种罕见侵袭性皮肤恶性肿瘤梅克尔细胞癌患者中进行了瘤内研究,无论是新辅助治疗,还是用于转移患者,均观察到客观肿瘤消退[4]。在一项对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的I/II期试验中,G100联合低剂量照射,联合或不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或利妥昔单抗,安全性良好,ORR为26%。且癌细胞TLR4表达水平较高患者更容易应答[5,6]。
4)TLR3激动剂
TLR3通过识别双链RNAs(dsRNAs)介导抗病毒反应。TLR3在免疫细胞、非免疫细胞以及多种肿瘤组织都有表达,与肿瘤治疗和预后相关。
TLR3激动剂聚胞苷:多胞苷酸(polyI:C)是一种人工合成dsRNAs类似物,是多种白细胞生成IFNα/β的强效诱导剂。
目前有三种基于polyI:C分子的TLR3激动剂已进入临床研发阶段:rintatolimod、Hiltonol和BO-112。
据报道,瘤内注射Hiltonol可导致肿瘤控制,对于少数转移性实体瘤患者,与DC疫苗和放疗联合,可显著控制疾病,未治疗病灶也有应答;然而,由于缺乏随机研究,无法得出疗效结论[7]。
在小鼠模型中,肿瘤内注射BO-112具有抗肿瘤活性[8]。在人类中,反复瘤内注射BO-112是安全的,可诱导I型IFN转录特征和CD8+T细胞浸润到注射部位病变中[9]。
5)CGAS/STING激动剂
环磷酸鸟苷-腺苷合成酶(cGAS)/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可通过胞质双链DNA,发现病毒或细菌感染或严重组织损伤。恶性肿瘤的细胞质中双链DNA片段多于正常细胞,因此CGAS/STING通路激活几率增加,进而产生抗肿瘤免疫作用。此外,cGAS/STING信号对放疗的免疫刺激作用也很重要,包括与免疫检查点抑制联合使用时引发远隔效应。
在小鼠体内,瘤内注射环二核苷酸vadimezan(也称为DMXAA)可促进抗肿瘤免疫,包括对非注射肿瘤的系统免疫,同时使用PD-1抑制可进一步增强免疫[10]。
还有其他肿瘤内给药人STING环二核苷酸激动剂已进入临床试验,单药治疗安全性良好,但抗肿瘤活性低,即使重复注射也是如此。
局部使用STING激动剂联合全身性抗PD-1单抗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一项涉及66例实体瘤患者的I期研究中,反复瘤内注射STING激动剂MIW815(ADU-S100)联合抗PD-1单抗spartalizumab安全,少数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或抗PD-1单抗耐药黑色素瘤患者可诱导客观应答[11]。类似地,在一项I期研究中,另一种瘤内TING激动剂MK-1454,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单抗耐受性良好,但临床活性有限[12]。
到目前为止,被寄予厚望的STING激动剂尚且难以令人满意。具有潜在不同作用机制的新型瘤内给药STING激动剂正在临床开发中,包括用于淋巴瘤和实体瘤的E7766。另一种瘤内给药新型STING激动剂BMS-986301,正在与纳武利尤单抗+伊匹单抗联合,在各种实体瘤患者中开展研究。
6)局部细菌免疫疗法
一种与柯利毒素密切相关的局部细菌免疫疗法OK-432(化脓性链球菌菌株的冻干混合物),依然是肿瘤的标准疗法。
OK-432目前已在日本、台湾和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淋巴管瘤。在非小细胞肺癌恶性胸腔积液患者中,一项随机II期试验显示,10 Klinische-Einheit(KE)给药第8天的病变控制率为79%,1KE93为53%[13]。对16例转移性结直肠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患者(13例腹水,3例胸腔积液)的回顾性分析中,穿刺时单独局部应用OK-432(0.2–5KE)或联合IL-2(100000IU),11例中的7例(64%)和5例患者中的4例(80%)胸腔积液长期消失[14]。
尽管OK-432具有很好的活性,但尚缺乏该药品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的研究。
(2)免疫原性肿瘤细胞毒性药物 直接向肿瘤细胞开炮
1)溶瘤病毒
溶瘤病毒可优先感染和杀死癌细胞,而对非恶性细胞无损。FDA和EMA批准的第一个溶瘤病毒talimogene laherparepvec(T-VEC),是一种经基因改造的单纯疱疹病毒-1(HSV-1),降低了其致病性,并编码人类GM-CSF。肿瘤内注射T-VEC已批准用于治疗IIIB-IVM1a期(EMA)或IIIB-IVM1c期黑色素瘤(FDA)患者的浅表性黑色素瘤转移。
重要的是,T-VEC联合抗CTLA-4和抗PD-1单抗用于治疗黑色素瘤,并未引起更多安全问题,抗肿瘤活性良好。目前正在进行III期试验,以确定这种联合疗法对IIIB-IVM1c期黑色素瘤患者的疗效是否优于抗PD-1单药。
编码GM-CSF的新型疱疹病毒载体,带有额外的免疫增强转基因(例如编码CD40L或4-1BBL),目前正进行肿瘤内给药的研发。编码GM-CSF的疱疹病毒RP1,已有早期证据证明其生物学和临床活性[15]。
Pexastimogene devacirepvec(Pexa-Vec)是处于临床研发阶段的第二个溶瘤病毒。为经基因改造的痘病毒,可编码GM-CSF。该药主要在肝细胞癌(HCC)中开展研究,通过诱导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对注射和非注射部位肿瘤都有临床活性[16,17]。目前,肿瘤内Pexa-Vec联合肿瘤内伊匹单抗以及静脉注射抗CTLA4或抗PD-1单抗,正在开展早期研究。然而,据报道,肿瘤内Pexa-Vec联合索拉非尼vs单独索拉非尼的III期研究PHOCUS为阴性[18]。
在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瘤内注射溶瘤腺病毒DNX-2401和teserpaturev产生了有希望的结果[19,20]。
目前正在开发新一代“荷枪实弹”的溶瘤病毒,可编码其他免疫刺激细胞因子、共刺激配体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目的是在全身或肿瘤内给药后可原位联合免疫治疗。在小鼠中,瘤内注射编码IL-7和IL-12的溶瘤痘病毒,可将免疫原性差的肿瘤转化为炎症肿瘤,并诱导完全消退,即使在远处的未注射的肿瘤部位也是如此[21]。
事实上,溶瘤病毒能将各种免疫调节剂组合成单个免疫治疗产品的多功能平台。此外,正在努力将已批准的减毒病毒疫苗重新用于肿瘤内免疫治疗中。
2)溶瘤分子
除了溶瘤病毒外,一些分子也具有溶瘤特性,并能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但没有与使用致病性和/或转基因生物体相关的临床障碍。例如,肿瘤内化疗有相当多的经验,包括环磷酰胺、阿霉素、米托蒽醌和奥沙利铂,但其尚未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
PV-10是一种黄原染料孟加拉玫瑰的水溶性衍生物,其肿瘤内免疫治疗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22]。
Tigilanol tiglate是一种从枫丹草(红木)的种子中分离出来新分子。欧洲已批准其通过瘤内给药治疗犬的肥大细胞肿瘤,并已证明其对人类癌症具有活性。
溶瘤肽是另一类有趣的肿瘤内免疫疗法。其来源于天然抗菌肽,也具有抗癌活性。例如ruxotemitide,临床前数据表明,其通过激活CD8+T细胞和CD4+T辅助性1型(TH1)细胞应答增强肿瘤浸润,并诱导注射和非注射肿瘤的全身抗癌免疫[23]。一项I期研究表明,其对肉瘤具有一定临床活性。目前正在对晚期实体瘤患者进行研究,包括与全身性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使用。
(3)局部给药细胞因子 助力已存在的免疫反应
细胞因子全身(静脉或皮下)治疗,主要包括IL-2、IFNα或TNF,还有IL-7或IL-15,已在癌症患者中进行了广泛研究,以扩大预先存在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但总体疗效有限,与严重不良事件相关。
目前,正在重新构建新的工程细胞因子,局部给药,以提高其他免疫治疗的疗效,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目前在研究的包括IL-2、IFNγ、IFNα和IFNβ、IL-15、IL-12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联合使用。
(4)免疫刺激性单克隆抗体 局部给药减毒增效
对于抗PD-1或抗-PD-L1抗体,剂量、临床疗效和毒性之间尚未建立明确的关系。事实上,这些药物的作用机理完全依赖于拮抗,靶标饱和后,剂量过高不会额外带来明显的安全性威胁或更多有效性。
然而,对于其他免疫刺激单抗,剂量限制毒性阻碍了使用最佳治疗剂量。因此,这种免疫刺激单抗肿瘤内给药可能会增加治疗指数,同时减少全身暴露和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唯一经批准的抗CTLA-4单抗伊匹单抗,单药或联合抗PD-1单抗,更高剂量有更高临床疗效。
在静脉注射激动性抗CD137单抗urelumab后,肝毒性为一种剂量限制性毒性。
局部注射单克隆抗体在肿瘤组织内,一个主要问题是其停留时间是否足以发挥治疗活性。某些药物制剂可能有助于延长此类药物的局部生物利用度。例如,抗CTLA4单克隆抗体的缓慢原位释放,通过肿瘤内注射含有乙碘化油和聚(乳酸-乙醇酸)纳米颗粒乳剂来实现[24]。
(5)局部给药免疫细胞 直接增兵或帮助优化作战计划
可以从患者或供者中分离出免疫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T细胞和NK细胞,随后通过修改培养条件,或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扩增和操作,产生临床级细胞治疗。例如,许多用体外分化或直接分离的树突状细胞来制制作治疗性癌症疫苗的临床数据已经发表,但疗效还很有限。
另一种方法是在肿瘤内注射树突状细胞,使它们处于最佳位置,以更好遇到、处理和交叉递呈肿瘤相关抗原。这种策略的美妙之处在于,树突状细胞可能作为一种原位疫苗来协调内源性免疫应答。这种方法的临床研究报道很少,一些涉及在肿瘤内用药前将树突状细胞进行转基因。然而,在小鼠模型中已经获得了很好的结果,特别是基因工程表达IL-12的树突状细胞。尽管如此,该方法的首项临床研究显示,在HCC或胰腺癌患者中疗效有限[25]。
2、肿瘤与免疫双重靶向
目前已在使用几种生物技术策略,让免疫治疗的活性选择性靶向肿瘤组织。正在开发中的主要有两种方法:(a)CD3靶向双特异性抗体;(b)其他免疫调节生物分子,其在肿瘤组织和潜在引流淋巴结中选择性累积或选择性激活。
(1)双特异性T细胞接合器 强行让肿瘤细胞与T细胞狭路相逢
双特异性T细胞接合器(BiTEs)是各种形式的抗体制剂,能够同时与细胞表面肿瘤相关抗原以及T细胞受体(TCR)的CD3ε结合,以触发T细胞激活,通过TCR-CD3交联模拟抗原识别。这一原理是博纳吐单抗有疗效的理论依据,一种抗cd19/CD3 BiTE已批准用于治疗恶性B细胞肿瘤。
针对实体肿瘤开发BiTEs,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设别肿瘤特异性细胞表面抗原。目前,多个T细胞接合器已在实体肿瘤患者中开展研究,包括靶向肿瘤相关蛋白EpCAM或CEA的药物,或来源于gp100、NY-ESO-1、MART-1或MAGE-A3的MHC I呈现的肿瘤相关抗原。
对于这些药物,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全身性炎症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因此,未来T细胞接合器可能进行肿瘤内试验,利用其靶向特点,以在肿瘤组织中首过保留,最大限度地破坏肿瘤细胞,同时潜在降低毒性风险。
(2)免疫-细胞因子和探针 为免疫治疗加上导航
另一种在肿瘤局部刺激免疫细胞的策略,是通过基因或化学方法,将细胞因子与靶向肿瘤中富集部分的抗体融合,以增强肿瘤微环境中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全身毒性。首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免疫-细胞因子”为IL-2与靶向神经节苷脂GD2的单抗相连接,该单抗在神经母细胞瘤细胞表面过度表达[26]。
TGFβ是参与促进上皮-间充质转化和诱导免疫抑制Treg细胞的一个关键细胞因子,它支持肿瘤进展。随着双曲抗体(bintrafusp alfa)的发展,TGFβ原位靶向已经成为可能,已经融合肿瘤靶向抗PD-L1抗体(阿维单抗)与TGFβ受体陷阱。值得注意的是,该药物在HPV相关癌患者中产生了39%的ORR[27]。
四、未来展望
直接瘤内给药可通过减少全身暴露,最大限度地提高免疫调节疗法的治疗指数。原则上,这种原位免疫刺激的方法是将肿瘤作为自身疫苗,激发或增强预先存在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然而,大多数肿瘤内免疫治疗初步研究收集的临床、放射学和生物学数据,并不能准确分辨局部和远处应答;因此,辨别注射和非注射肿瘤的这些效应,是未来研究的关键目标。
PD-1或PD-L1抑制剂,尽管局部给药的治疗价值很大程度尚不清楚,但可能在全身给药时最有效。尽管如此,临床前和临床证据表明,PRR激动剂和溶瘤病毒局部给药时更为活跃,并可能与全身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具有协同作用。这些策略目前正在进行III期研究。
肿瘤内免疫治疗可直接或在图像引导下注射;因此,局部免疫治疗的疗效可能取决于操作人员,取决于原位给药的质量。这导致,该方面的技术是肿瘤内治疗大规模发展的一个严重挑战。
新的局部免疫治疗策略和相关药物正在彻底革新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和治疗。然而,这些方法对后勤带来了复杂的挑战,肿瘤学实践的模式亟需改变。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北京诺默斯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内容由环球医学独立编写,其观点并不反映优医迈或默沙东观点,此服务由优医迈与环球医学共同提供。
如需转载,请前往用户反馈页面提交说明:https://www.uemeds.cn/personal/feedback
[1] Ribas, A. et al. SD-101 in combination with pembrolizumab inadvanced melanoma: results of a phase Ib, multicenter study. Cancer Discov. 8,1250–1257 (2018)
[2]Haymaker, C. et al. Final results from ILLUMINATE-204, a phaseI/II trial of intratumoral tilsotolimod in combination with ipilimumab in PD-1inhibitor refractory advanced melanoma [abstract 1083MO]. Ann. Oncol. 31(Suppl. 4), S736 (2020)
[3] Adams, S. et al. Topical TLR7 agonist imiquimod can induceimmune-mediated rejection of skin metastase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Clin. Cancer Res. 18, 6748–6757 (2012)
[4] Bhatia, S. et al. Intratumoral G100, a TLR4 agonist, induces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s and tumor re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Merkel cellcarcinoma. Clin. Cancer Res. 25, 1185–1195 (2019).
[5] Flowers, C. et al. Intratumoral G100 induces systemic immunityand abscopal tumor re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follicular lymphoma: results ofa phase 1/2 study examining G100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pembrolizumab[abstract]. Blood 130 (Suppl. 1), 2771 (2017)
[6]Flowers, C. R. et al. Long term follow-up of a phase 2 studyexamining intratumoral G100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pembrolizumab in patientswith follicular lymphoma [abstract]. Blood 132 (Suppl. 1), 2892 (2018)
[7] Rodriguez-Ruiz, M. E.et al. Combined immunotherapy encompassing intratumoral poly-ICLC,dendritic-cell vaccination and radiotherapy in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Ann.Oncol. 29, 1312–1319 (2018)
[8] Aznar, M. A. et al. Immunotherapeutic effects of intratumoralnanoplexed poly I:C. J. Immunother. Cancer 7, 116 (2019).
[9] Marquez-Rodas, I. et al. Intratumoral nanoplexed poly I:CBO-112 in combination with systemic anti-PD-1 for patients withanti-PD-1-refractory tumors. Sci. Transl Med. 12, eabb0391 (2020).
[10] Corrales, L.et al. Direct activation of STING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leads topotent and systemic tumor regression and immunity. Cell Rep. 11, 1018–1030 (2015)
[11] Meric-Bernstam, F.et al. Phase Ib study of MIW815 (ADU-S100) in combination withspartalizumab (PDR001) in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metastatic solid tumorsor lymphomas [abstract]. J. Clin. Oncol. 37 (Suppl. 15), 2507 (2019).
[12] Harrington, K. J.et al.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first-in-human (FIH) study of MK-1454,an agonist of 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 (STING), as monotherapy or incombination with pembrolizumab (pembro)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or lymphomas [abstract LBA15]. Ann. Oncol. 29 (Suppl. 8), viii712 (2018).
[13]Kasahara, K. et al. Randomized phase II trial ofOK-432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due to non-small cell lungcancer. Anticancer Res. 26, 1495–1499 (2006)
[14] Yamaguchi, Y. et al. Locoregional immunotherapy of malignanteffusion from colorectal cancer using the streptococcal preparation OK-432 plusinterleukin-2: induction of autologous tumor-reactive CD4+ Th1 killerlymphocytes. Br. J. Cancer 89, 1876–1884 (2003)
[15]Middleton, M. et al. An open-label, multicenter,phase 1/2 clinical trial of Rp1, an enhanced potency oncolytic Hsv, combinedwith nivolumab: updated results from the skin cancer cohorts [abstract 422]. J.Immunother. Cancer 8 (Suppl. 3), A257 (2020)
[16] Heo, J. et al. Randomized dose-finding clinical trial ofoncolytic immunotherapeutic vaccinia JX-594 in liver cancer. Nat. Med. 19,329–336 (2013)
[17]Kim, M. K. et al. Oncolytic and immunotherapeuticvaccinia induces antibody-mediated complementdependent cancer cell lysis inhumans. Sci. Transl Med. 5, 185ra63 (2013).
[18] . Transgene. Transgene provides an update after the interimfutility analysis of the PHOCUS study of PexaVec in liver cancer. Transgenehttps://www.transgene.fr/ en/news/#pressreleases (2019)
[19] Lang, F. F. et al. Phase I study of DNX-2401 (Delta-24-RGD)oncolytic adenovirus: replication and immunotherapeutic effects in recurrentmalignant glioma. J. Clin. Oncol. 36, 1419–1427 (2018)
[20] glioma. J. Clin. Oncol. 36, 1419–1427 (2018). 110. Rosa, K.Japanese approval sought for oncolytic virus teserpaturev for malignanatglioma. OncLive https://www.onclive.com/view/japanese-approval-soughtfor-oncolytic-virus-teserpaturev-for-malignant-glioma(2021)
[21]Nakao, S. et al. Intratumoral expression of IL-7and IL-12 using an oncolytic virus increases systemic sensitivity to immunecheckpoint blockade. Sci. Transl Med. 12, eaax7992 (2020)
[22]Read, T. A. et al. Intralesional PV-10 for thetreatment of in-transit melanoma metastases –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non-randomized, single center study. J. Surg. Oncol. 117, 579–587 (2018).
[23]Baurain, J. F. et al. A phase I study of theoncolytic peptide LTX-315 generates de novo T-cell responses and clinicalbenefit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arcoma [abstract]. Cancer Res. 79 (Suppl.13), CT010 (2019)
[24]Tselikas, L. et al. Pickering emulsions withethiodized oil and nanoparticles for slow release of intratumoral anti-CTLA4immune checkpoint antibodies. J. Immunother. Cancer 8, e000579 (2020)
[25]Mazzolini, G. et al. Intratumoral injection ofdendritic cells engineered to secrete interleukin-12 by recombinant adenovirus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gastrointestinal carcinomas. J. Clin. Oncol. 23,999–1010 (2005)
[26]Voeller, J. et al. Combined innate and adaptiveimmunotherapy overcomes resistance of immunologically cold syngeneic murineneuroblastoma to checkpoint inhibition. J. Immunother. Cancer 7, 344 (2019)
[27]Navid, F. et al. Phase I trial of a novel anti-GD2monoclonal antibody, Hu14.18K322A, designed to decrease toxicity in childrenwith refractory or recurrent neuroblastoma. J. Clin. Oncol. 32, 1445–1452(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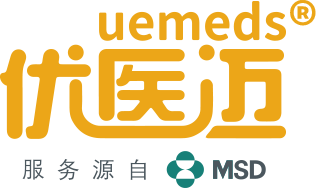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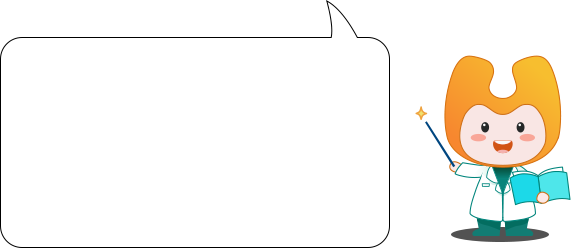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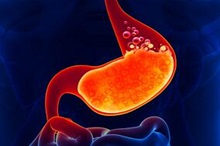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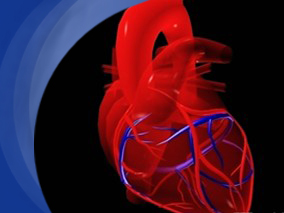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3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3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