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名医生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所有医生都会犯错。阿图•葛文德,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哈佛医学院临床外科副教授,是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对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医患问题,阿图•葛文德用自己的实际经历探讨年轻的医生如何在不危急病人生命的前提下获得更多实践经验?
学生时代:第一次拿外科手术刀异常紧张
差不多二十年前,阿图•葛文德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有一次,他去观摩一台手术。当时外科医生在熟睡病人的肚皮上画了一条15厘米的线,护士居然把手术刀递给了葛文德。很多年以后,葛文德医生回想起那一幕,依然记得自己当时有多紧张。那把手术刀刚经过消毒,还是温热的。外科医生对他说了一句:“一刀切到脂肪层。
“我把刀锋放到病人的腹部,皮肤很厚并且富有弹性,我的第一刀力气不够,切得不够深,不得不再补了一刀。”葛文德回忆,正是这短短几分钟,让自己确信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这种感觉太奇妙了,使人上瘾”。
住院医生:漫长的彷徨以及对自身职业的困惑
那一刀带来的奇妙感觉之后,葛文德在做住院医生后有过漫长的彷徨以及对自身职业的困惑。于是他开始写作。作为住院医生,他可以从特殊的局内人的位置看待医学,这是很重要的。医学并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而是一个时刻变幻、难以琢磨的知识系统。每天,外科医生都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情况:信息不充分,科学理论含糊不清,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永远不可能完美。即便是最简单的手术,医生也不可能向病人保证手术后一定会比原来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外科手术好像是一种方法,用来探索医学的不确定及其难题。即使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也深深认识到,科学和人类技术是有限的。
年轻医生如何在不危急病人生命的前提下获得更多实践经验?
在葛文德出版的中文版名为《阿图医生第1季》的作品集里,14篇短文中,葛文德以一个年轻医生的现实感受,试图谈论医学背后更为深刻的伦理问题:年轻的医生,如何在不危急病人生命的前提下获得更多实践经验?医生们究竟该对“医疗事故”承担多大的责任?
葛文德描述的诸多案例记录了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成长。刚开始,他会向病人介绍“我是葛文德,外科实习医生。将由我来协助进行这次手术”,偶尔有人震惊:“我不想让实习医生给我开刀。”通常的做法,他会安慰:“别担心,我只是助手,有主治医生操刀。”
但那只是一种模凌两可的“托词”。“我并没有说谎,手术中都有主治医生负责,他们才是决策者。但是,如果说我只是助手也不符合实情。毕竟,我在手术中并不是为主治医生打下手的。否则,为什么是我拿着手术刀?为什么是我以手术医生的身份站在手术台边?为什么要升高手术台来配合我的身高?我是个帮忙的,但同时我也在练习。”葛文德写道。
外科手术像其他手工技艺一样,技巧和信心都从经验中累积而来,但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医生是用活人做练习。矛盾的是,病人也希望医生技术不断成熟和进步,但是没有人愿意面对技术进步的前期代价—即便是角色转换后的医生自己。
一位公共健康专家曾与葛文德争论过这个矛盾。在那一次讨论中,专家坚持认为:“大多数人会理解医生的苦衷。我们应该对病人说出实情,人们肯定愿意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但是当葛文德指着专家办公桌上的小孩照片问:“您的小孩是住院医生接生的吗?”专家沉默片刻,终于承认:“不是,我甚至不允许住院医生进产房。”
葛文德医生自己也面临过如此尴尬的抉择。出生11天的小儿子威利突发充血性心脏衰竭,被送进手术室。尽管修补手术很成功,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主治医生提醒为人父的葛文德,应该为威利选择一位小儿心脏病外科专家作为家庭医生,跟踪观察威利的病情。
“出院前一天,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找到我,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希望成为威利的家庭医生。在整个治疗威利的团队中,他是最尽心尽力的一位。大多数人不知道医生其实是分不同等级的,当一个医生救了他们孩子的命,他们就想尽办法预约这位医生。但我知道这些区别。”尽管当时自己同样是一位“住院医生”,葛文德还是说出了那句话:恐怕我们想找的是纽伯格医生。纽伯格医生是这家医院心脏外科的副主任,对威利的病情更富有经验。
“所以说,住院医生有时候只有使用托词,才能让病人相信他,将身体交给他,住院医生也才能有学习的机会。”葛文德说,美国医院里的机制几乎都是在以一种“不征求病人意见”的前提下,将很多事情交给需要练习的住院医生做的——他们拒绝给病人以选择的机会。这种“冷血机制”的好处不只是提供新手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保证了公平——如果学习中一定会造成伤害,那么这种概率应该对每个人都一样。
医患对立的缘由:被放大的医疗过失
公众会认为医疗过失是由于某些医生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这样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而且每个医生都有可能出现过失。
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把一支很大的金属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结果病人的肠子和膀胱都被刺破了;另一位肿瘤外科医生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检查,却搞错了地方,使其癌症诊断拖延了数月;还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碰到一个腹部剧痛的病人,他没做电脑断层扫描,就认定病人患有胆结石,18个小时后,扫描结果显示病人腹部动脉瘤破裂,没多久就死了。
葛文德表示,这些国内被“曝光”、“揭露”的似曾相识的案例,同样在美国发生。因为医疗过失,美国的医生们也必须面对医疗官司、媒体曝光、停职处分,甚至被解雇。根据相关统计,美国每年至少有44000个病人死于医疗事故。
在医生这个行当中,有一件事毋庸置疑:所有的医生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葛文德说,“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坏医生身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葛文德自己也曾因“过失”让人命悬一线,这个故事被他用“切烂的喉咙”为题,记录在书中。一名34岁的女性酒醉驾车,车速过快而翻覆,抵达急诊时已经昏迷。可能由于呼吸道阻塞,急诊插管数次,没有成功。因值班主治医生在进行另一台手术,需要当时作为住院医生的葛文德进行气管切开术——在此之前,他从未做过气管切开术——尝试数次后,葛文德还是失败了。而病人缺氧若达四分钟,即便不死也会导致脑部永久性损伤。最终,一位经验丰富的麻醉科医生用儿科用气管插管成功,病人后期检查也显示并没有造成脑部永久性损伤,但这事对于葛文德来说,刻骨铭心。
“病人比飞机更具有独特性,也更复杂。医学也不是生产线,更不是产品目录,它比人类涉足的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复杂。”葛文德试图解释医学中错误发生的频繁,“如果一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必须依赖完美的表现,那么很多错误会伺机冒出来。”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开处方。这是一个常规程序,记忆力和专注力在其中至关重要—但人类的记忆力却并不可靠。无可避免,医生总会有开错药或者开错剂量的时候。即便处方签写得完全正确,药师拿药的时候也可能看错或者拿错。与此同时,医生工作量普遍过大,或者急诊现场混乱、医疗团队成员沟通不足产生误解,都可能成为医疗体系中潜在错误的发生源。
“其实医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那些提出医疗诉讼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医疗过失的受害人。而医疗官司最终能否打赢,主要取决于原告病人的状况有多惨,而非这个结果是不是由医疗过失所造成的。”葛文德进一步指出,有关医疗官司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若把过失放大化,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问题,那么医生当然会拒绝公开承认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扭曲的制度会造成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敌对关系。
医学是复杂的,医生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患者的理解!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北京诺默斯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内容由环球医学独立编写,其观点并不反映优医迈或默沙东观点,此服务由优医迈与环球医学共同提供。
如需转载,请前往用户反馈页面提交说明:https://www.uemeds.cn/personal/feedb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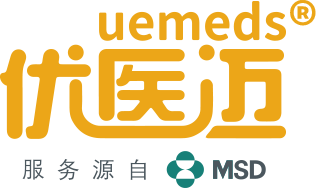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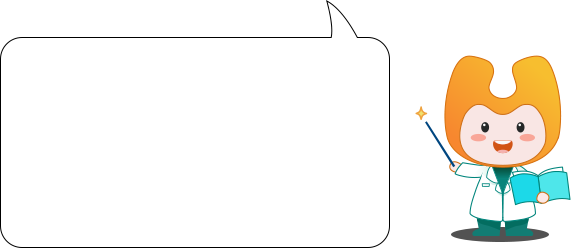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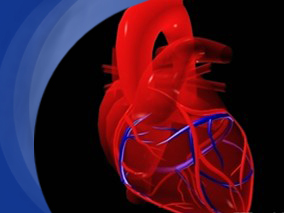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