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存在过这个世界上而被避而不谈的历史事件称之为黑历史。医学黑历史更是不胜枚举。在医学的发展中,研究者强烈的进取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也时常冲破道德底线,给人性刻下丑陋的疤痕。医学实验正是这些黑历史的重灾区。
纳粹人体医学实验
遗传研究基金会这个听起来如此普通的名字,却是纳粹分子做一些神秘的医学实验和研究,骇人听闻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的直接领导者就是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1941年秋天,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斯拉乌塔市,并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收容有病的红军官兵的军医院,称为斯拉乌塔“军医院”301分营。就是在这所被人讽刺为“军医院”的死亡集中营中,纳悴医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蓄意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他们把那些患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的病人同受轻伤和重伤的人塞进一幢房子甚至同一间病房里。在通常只能安置四百人左右的地方,有时竟塞进一千八百名患伤寒、肺结核的病人。病房已经长时间没有打扫过,生病的战俘在好几个星期里都穿着被俘时穿的内衣裤,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褥床单,许多人甚至赤身露体。房间里从来没生过火,俘虏们自己盘的简易炉子也塌了。这里没有洗脸的水,甚至连饮用水也没有,这种损害身体健康的状况,使军医院里虱子滋生猖獗。而故意让传染病蔓延,将无病战俘同患传染病战俘关在一起的做法使“军医院”常常发生莫明其妙的流行病,德国医生称之为霍乱。这种病的流行就是德国医生所做的各种实验的野蛮结果。这些流行病常常自生自灭。霍乱病例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员后来都以死亡告终。一些死于这种病的人被德国医生解剖了。但俄国战俘中的医生想对同胞死者进行验尸却被党卫队员坚决制止。有些时候,法西斯罪犯常常没有耐心等待这个或那个战俘咽气,许多战俘是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活埋了。在死者的呼吸器官深部,甚至最纤细的支气管里,人们发现战俘死亡时曾吸进砂粒。更多的时候,德国的教授和医生以治疗为借口在红军官兵身上进行各种生物制剂、化学制剂及其他各种试验,受伤战俘因此而遭受脓毒性感染,随后就死去了。在斯拉乌塔被占领的两年里,希特勒分子大约消灭了十五万名红军官兵。医生博尔贝博士和施图姆博士以及其他医院人员在这方面为纳粹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中有许多是有相当造诣的医学人士,而可悲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毒雾下,这些白衣天使蜕变成了磨鬼,成了纳粹屠杀战俘的帮凶。
在这种蓄意谋杀事件中,虽然参与试验的还不到二百名医生—其中有些人在医学界有甚高的地位,但因为没有了医德,他们就类同于甚至赶不上江湖混子或骗子。但是,令人遗愿的是,在德国,虽然有成千上万名一流的医生知道他们同行的罪行,但这些医生中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哪怕最轻微的抗议。因此有人说,德国新秩序期间,德国医生队伍本身就是一台毫无知觉的“死亡机器”。在死亡机器制造的死亡中,丧失生命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还利用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女囚犯,甚至德国人进行试验。试验是多种多样的,囚犯有的被用于压力试验、耐高温试验,直至停止呼吸,有的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有的被用于冷冻实验,被浸在水中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致冻死;还有的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拉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瓦乐德,吉普赛人被挑选出来用于“唱盐水究竞能活多长时间”的试验。在几个集中营中,曾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绝育试验。在1942年的冬天,从柏林来到奥斯威辛的舒曼教授在女营中装备了一座X光实验站,用强X光射线的照射来使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丧失生殖能力。目的是“使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绝育,这样既可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消除给帝国增添的无谓的负担。“为此目的,集中营当局向舒曼教授提供了无法统计的犹太犯人。
灭绝生殖能力的手术是这样进行的:将犯人放在X光机的圆锥形灯泡之间,持续照射好几分钟。这种做法,令犯人们很痛苦,他们常常喊叫起来。选去作绝育手术的是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囚犯,主要是荷兰和希腊犹太人。前后共有数十人作了这种手术。这些犯人在照射后很快就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另外,党卫队医生舒曼还给女人做绝育。为此,他桃选了年轻貌美的萨罗尼加希腊少女做试验对象,先用X光照射卵巢部位,然后作切除卵巢的手术。数周后,当刀口有几分愈合时,女犯人又得作一次手术,切除另一例的卵巢。曾有一次,参加绝育手术的德林格医生和另一名党卫队医生打赌,说他半天之内能给十名妇女做手术,结果,他打赌赢了。但是这些妇女在手术完刚被带走后就倒了下来,死因是德林格在手术时为了争输赢,草率从事,结果大多数妇女内出血导致死亡。另一个罪大恶极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不知道怎么对研究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头盖骨发生了兴趣。他在1941年写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的信中说: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劣等民族的标本头盖骨,现在我们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把这些犹大人弄死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送来。希尔特博士的请求,得到希姆莱的支持,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希尔特得到了充足的供应,供应者就是外号叫“纳粹蓝胡子”的纳粹分子沃尔弗莱姆·西佛斯。西佛斯于1943年6月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七十九名犹太男子、三十名犹太女子、四名亚洲人和两名波兰人,总共一百一十五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作特别处理。
党卫队老牌凶手,曾以”贝尔森野兽“而威震一时的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尔承担了这项处决任务。他反复做了几次,直到把这些囚犯都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了希尔特教授。后来,希尔特教授又收到了标有“军事物品”字祥的两批囚犯的尸体,共五十六具男尸。但是在希尔特教授做完这些囚犯的尸体模型之后,因为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教授的科学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没有销毁的几具尸体。最为惨绝人寰的当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搜集人皮的事件。专门为这个残忍的目的而处死囚犯从而剥下人皮的做法,不能用“科学研究”作借口。这些人皮是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的,它们具有极高的装饰价值。因此有人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了几只人皮灯罩。这个掌握布痕瓦尔德囚犯们的生杀大权、被囚犯们称为“布痕瓦尔德媳妇”的科赫夫人最喜欢纹身的人皮。因此……所有纹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将其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处理。成品送给科赫夫人,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饰品。据说,科赫夫人最为喜爱的一片人皮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在达豪集中营,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说: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是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就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勃拉哈博士提到的这个腊彻尔博士是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人,他所进行的高空试验及冷冻试验可说是对囚犯的残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做高空实验时,腊彻尔博士亲自观察研究,亲自解剖,他用二百多名囚犯进行这种试验后,才结束了这项工作。而他所创造的囚犯惨死时的情况更令人咋舌: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缺氧时的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试验进行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者失去了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三十分钟,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这些试验总是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实验是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他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极限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的办法。他选用两种冻死人的办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手下担任护士,他作为外行人对腊彻尔博士的冰冻试验作了描述: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扒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整整呆了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的情况最多只能呆上六十分钟就失去知党。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回答说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话翻译给腊彻尔听。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位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腊彻尔所做的冷冻试验,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荒诞。在腊彻尔的试验中共有三百多人被用来进行约四百次“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有的发了疯,有极少数人因担心泄露试验内容而被杀死。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些医学试验对人的迫害证据确凿,对囚犯所犯下的罪行万恶不赦,但有很多凶手,像想使干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波科尔尼却被宣判无罪。而更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听腊彻尔宣讲《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的论文时,在场所有的人,包括医学界著名的九十五名德国科学家,在毫无疑问地知道腊彻尔杀害了许多人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难怪乎人们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时议论:整个德国医学界在新铁序运作期间都像人皮事件的刽子手那样疯了,而纽伦堡的审讯判决官们也疯了。
美国:“法外之地”的道德困境
在崇尚民主和自由的美国,未经患者同意的不道德人体实验到二战以后依然时有发生。
1932年到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进行了著名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400名患有梅毒的贫困黑人男性被告知将得到治疗,但是显然这是一个谎言。研究人员只想观察梅毒对他们身体的长期影响。甚至当患者想通过其它途径寻求治疗时,也被调查人员想方设法阻止。最终,参加实验的患者28人死于梅毒,100人死于并发症,40个人的妻子被传染,19人的孩子得了先天性梅毒。当这项“医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体无治疗实验”结束时,只有74人幸存。
同塔斯基吉梅毒试验一样备受争议的,还有萨尔·克鲁格曼和他的乙肝疫苗实验。在从1963年到1966年,萨尔·克鲁格曼被指为了进行疫苗实验,迫使精神残疾儿童的父母签订一张声称为“接种疫苗”的程序知情同意书。如果家长不愿意,精神病院将不接收患儿。实际上,程序中包括通过让他们进食肝炎患者粪便中的提取物,故意染上病毒性肝炎。1981年,第一种经过FDA许可的血清乙肝疫苗在美国上市,数以千万人因此而不再被乙肝病毒所威胁。而萨尔·克鲁格曼自己,最终于1995年,在质疑和指责声中去世。
在美国发生的不道德人体实验大都是以贫困人群、黑人、精神残疾人群作为实验对象,涉及到外科、病菌、化学、放射性物质以及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这些实验对象作为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以及疾病知识上与研究机构和医生存在强烈的不对等,导致不道德的人体实验可以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找到一块任其滋长“法外之地”。
黄禹锡:一个民族英雄的倒下
2004年2月,黄禹锡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其研究成果轰动了全世界。
连续不断推出世界性的科研成果,黄禹锡被不少韩国民众捧为领导韩国科技未来的民族英雄,鲜花、掌声、荣誉不断飞来:2005年,首尔大学国际干细胞研究中心成立,黄禹锡担任主任;韩国政府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韩国政府向其研究小组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用于研究;黄禹锡成了一位韩国“国宝”级人物,甚至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镖服务。
2006年1月,神话破灭。一直负责验证黄禹锡教授科研组干细胞研究成果的首尔大学调查委员公布调查结果:黄禹锡在2005年5月刊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中的干细胞数据是伪造,伪造数据包括论文数据中的DNA指纹分析、畸胎瘤和胚胎照片、组织适合性、血型分析等。报告书显示,该论文宣称用患者体细胞克隆出的与患者基因吻合的11种特制型胚胎干细胞也不存在。
报告书还揪出另一个造假内幕。黄禹锡科研组200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关于用体细胞核置换方法培育干细胞的论文相关数据亦出自编造。据悉,黄禹锡科研组2004年发表的论文数据编造手法与2005年论文如出一辙。
尽管各种“假货”令人伤心,但是此次调查结果表明,还有一个研究结果令人感到安慰,就是克隆犬“斯纳皮”的确为体细胞克隆出来的产物
获过诺奖的神经科学“黑历史”: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被授予了葡萄牙医师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António Egas Moniz)以表彰他发明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然而仅仅不到一年,对莫尼斯的批判就超越了赞许,他赖以成名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也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受抵制。
通过手术治疗精神病并不算是一个很新颖的想法,从十九世纪末就已经有人陆续开始了这类尝试,但这些手术的效果大多并不尽如人意,不过莫尼斯还是决定要再试一次。1935年11月12日,就在莫尼斯从伦敦回去后不久,他于里斯本的圣玛塔医院(Hospital Santa Marta)做了第一次尝试,由于他本人的手因为痛风而不太灵活,所以手术实际上是在他的指导下由其助手利玛(Almeida Lima)完成的。他们小心地在病人颅骨上锯开一个口子,然后再通过这个开口向前脑叶当中注射乙醇来杀死那一片的神经纤维。手术之后,病人活了下来,并且症状有所减轻,尽管病人最终没有恢复到能出院的地步,但是莫尼斯依然宣称他的手术取得了成功。受此鼓舞,莫尼斯又接二连三做了更多类似的手术。非常幸运的是,莫尼斯前20例手术的病人都幸存了下来并且没留下太过严重的后遗症。
莫尼斯由于在早些年因为发明脑血管造影术(cerebral angiography)而在国际上颇有名望,因此他的工作刚一发表就在全世界备受关注。尽管不久后他就发现损伤前脑叶会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比如反应迟钝以及性格变化等,但他依然相信较之对精神病的出色疗效,这些副作用是可以被容忍的。同时,他也对手术进行了一系列改进,比如他发现用乙醇很容易殃及无关的脑区,故而专门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前脑叶白质切除器”(leucotome)的器械来机械损毁前脑叶的神经纤维。因此,这套手术方法后来被称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很快,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精神病院的医生仿佛迎来了曙光:只要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术,那些狂暴的患者就会变得像小宠物一样任人摆布。
然而,莫尼斯的方法需要给颅骨定位、钻孔等等复杂的程序,这不但大大延长了手术所需的时间,也对医生的技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需要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实在太多,而那时候大部分精神病院都不配备专业的手术室,精神病医生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加“好用”的方法。
1945年,一个美国医生沃尔特·弗里曼二世(Walter Jackson Freeman II)对这种“手术”进行了一项“改进”,他发明了所谓的“冰锥疗法”(ice-pick lobotomy),这种“手术”是真正意义上的“触目”惊心——医生直接用锤子将一根大概筷子粗的钢针从病人的眼球上方凿入脑内,而后徒手搅动那根钢针以摧毁病人前脑叶。这种手术不但简便快捷,而且还不需要很严格的消毒措施,当时精神病院里那些用来对付危险患者的束缚用具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一个临时的手术台,因而在发明之初便大受欢迎。
然而,随着手术的普及,尤其是“冰锥疗法”问世后,情况变得糟糕起来:由于这种手术既没有精确的定位,也没有标准的操作流程,医生往往是凭感觉对着病人大脑乱捣一气,所以术后病人的表现可谓千奇百怪。有些病人直接死于手术或是因为手术后遗症而自杀;有些人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残疾;也有一些出现了极端的狂躁或是抑郁症状;而最多的情况是,病人精神病症状有所减轻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些病人变得像行尸走肉一般,孤僻,迟钝,麻木,神情呆滞,任人摆布,从此一生就生活在无尽的虚无之中,一个母亲这样描述她接受过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女儿:“我的女儿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的身体还在我身边但她的灵魂却消失了。”最后,即便是前脑叶白质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四成病患得到了好转,剩下的要么毫无效果要么变得更糟。
更可怕的是前脑叶切除术开始遭到滥用,这也是该手术在今天声名狼藉的主要原因之一。精神病院的医生为了省事,开始没节制地给病人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那些饱受患有精神病的家庭成员折磨的家人也热衷于将他们得病的亲人送去接受这种手术。加上“冰锥疗法”的发明人弗里曼十分善于宣传,经常纠集一群记者搞一些“医疗秀”之类的节目来提高这种疗法的知名度,一时之间,前脑叶切除术变得非常流行。由于没有适当的管理,许多街边诊所也开始打出前脑叶切除术的招牌,用简陋的工具和只经过简单培训的人员来实施手术。
与此同时,手术的实施对象也从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扩展到了一切精神或行为有异常的人群,到最后如弗里曼之流甚至是来者不拒,都不问有病没病只要给钱就敢做,这种状况甚至连莫尼斯本人都有些看不下去。
到20世纪40年代后半段,情况变得愈发糟糕起来,声称可以“治疗疯狂”的前脑叶切除术本身却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和混乱中。由于媒体和广告的添油加醋,这种本该是治疗严重精神病的最后手段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俨然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在日本,许多小孩子被他们的家长送去做前脑叶切除术,而原因仅仅是家长觉得他们“不乖”。在丹麦,政府专门为这类“新型疗法”建造了大量医院,而针对的疾病则是从弱智到厌食症简直无所不包。在情况最严重的美国,由于弗里曼等人鼓吹“精神病要扼杀在萌芽状态”,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经过仔细检查就被拉去做了这种手术。更有甚者将这种手术用在了暴力罪犯和政治犯身上。
翻看那个时代的病历,不难发现许多令人扼腕的悲剧。《华尔街日报》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披露,在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美国政府曾对一批遭受战后精神创伤的退伍军人集体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遭受了伴随其一生的严重后遗症。
1941年,当“冰锥疗法”还没被发明的时候,弗里曼为一个叫做罗斯·玛丽·肯尼迪(Rose Marie Kennedy)的女病人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以治疗她的智力障碍。这位肯尼迪小姐,便是著名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亲姐姐。手术的结果堪称相当糟糕,肯尼迪小姐手术后智力不增反降,成了一个整天只会发呆的“木头人”。虽然弗里曼本人也因此遭到了不少指责,但他反倒因此在民间名声大噪,来向他寻求医疗帮助的民众更加趋之若鹜。
在种种非议声中,莫尼斯还是因为这种手术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这无异于是对前脑叶切除术最强大的广告,将这种癫狂带向了最高潮。真可谓“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面对种种异状,最先反应过来的也是科学界。早在1944年,《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就撰文认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会导致病人出现暴力倾向或是奴性和盲从。1947年,瑞典精神病理学家斯诺里·沃法特(Snorre Wohlfahrt)更是多次强调“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过于危险,不适合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或是其它精神症状。”但是,在一片狂热的喧嚣中犹如苍茫大海中的浪花,很快就湮灭无闻了。
但随着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入,额叶皮层与丘脑以及边缘系统的功能联系逐渐被揭秘。在这些新证据下,越来越多科学家意识到,简单地损毁前脑叶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联系会对人格造成不可逆且不可知的损害。加之许多真正对精神分裂症有效的药物,如氯氮平、利培酮等被开发出来。终于,在1950年,在苏联精神病理学家瓦西里·加雅诺夫斯基(Vasily Gilyarovsky)的强烈建议下,苏联政府最先宣布全面禁止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到1970年,绝大多数国家,以及美国许多州都已立法禁止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讽刺的是,直到1977年,卡特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国会设立的“国家生物医学与行为学实验人类保护项目大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依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限制性地使用一些极端治疗手段,如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可以起到积极的疗效。”
亡羊补牢了,但病人及其家庭的痛苦却已经无法挽回。据统计,单单在1939到1951年间,美国就有超过18000人接受了这样的“手术”,而全世界范围内有此遭遇者更是数以万计。
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其实人类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切悲剧的。就在莫尼兹得诺贝尔奖的一百年前,一个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P. Gage)的铁道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在爆破中,他被一根铁棍从下往上穿过头部。受此影响,他的一部分大脑永久性地遭到了损坏,而这个脑区正是后来前脑叶白质切除术重点捣毁的前额叶。
经过全力抢救,盖奇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伤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他除了瞎了一只眼睛(被铁棒穿过时连带损伤)以外,其语言、记忆、运动等技能都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他却性情大变,从一个友善而坚定的好人变成了一个傲慢,专横,优柔寡断且没有丝毫羞耻之心的人渣。直到一百多年后,科学家才了解到前额叶皮质与人的情绪、价值判断和复杂决策等高级思维活动直接相关,可以说是大脑的命令中心。
尽管盖奇的案例也名动一时,可是并没有太多人由此开始了解前额叶的功能,甚至是后来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甚嚣尘上的时候,一些病人出现了类似盖奇的症状,也没有几个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现在回头想想,实在感到莫大的遗憾。
思考
可以说,一些“悲剧”铺就了通往现代医学的血泪之路。
与所有实用技术一样,医学也需要严谨的理论基础。然而面对一些重大疾病的时候,医学有时候会暂时跳过理论以“经验技术”的形式去解决燃眉之急。但是没有扎实理论依托的技术终究是难以完美的,一旦理论跟进,那些经验技术的短板就会显露出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去反思那段疯狂的岁月,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神经科学早已今非昔比。
在我们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医学是经历了无数磨难,付出了巨大代价,走了许多弯路才发展到今天的。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北京诺默斯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内容由环球医学独立编写,其观点并不反映优医迈或默沙东观点,此服务由优医迈与环球医学共同提供。
如需转载,请前往用户反馈页面提交说明:https://www.uemeds.cn/personal/feedb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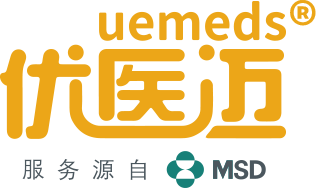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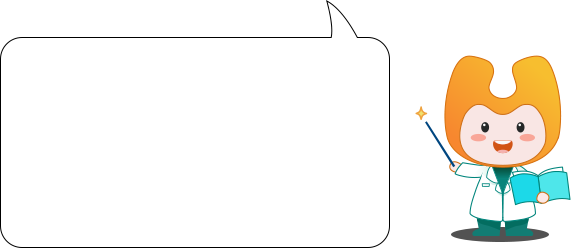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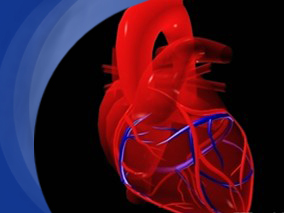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