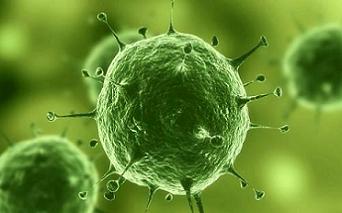世卫组织9日发布埃博拉疫情最新通报,称疫情已经造成近2300人丧生。利比里亚的疫情面临大幅蔓延扩散,未来三周可能会新增数千病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计划在即将于本月开始举行的新一届联大期间紧急召集有关应对埃博拉疫情的高级别会议。埃博拉病毒被发现已近40年,当前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最严重和最复杂的一次。埃博拉病毒,何处寻“解药”?
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世卫的数据显示,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等国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至少2296人死亡,病例数达到4293例。
上述有关病例统计未将利比里亚的新增病例列入。利比里亚的疫情面临大幅蔓延扩散。世卫组织警告说,在今后3周内,预计利比里亚还会增加“数以千计”的新病例,因此希望国际社会做好准备,把援助力度“增至三四倍”。
世卫官员透露,用传统治疗措施已经难以控制埃博拉疫情在利比里亚的蔓延。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病毒治疗机构现在已经人满为患,而这些机构已无法应对更多患者。
世卫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司长布里安德9日承认疫情病例数统计目前被低估。
其他地区
刚果(金)卫生部9日证实,刚果(金)已有35人死于埃博拉出血热,另有14人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者和确诊者均在刚果(金)赤道省杰拉地区,另有22例高度疑似病例和26例疑似病例。
印尼棉兰一位病患者9日晚在北苏门答腊省医院因发高烧死亡。该患者近日从尼日利亚返回印尼不久,医院怀疑患者可能已感染埃博拉病毒。当地媒体10日报道称,这位患者57岁,名字和性别尚未披露。
意大利卫生部门9日证实,意东部马尔凯大区当天发现一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目前疑似患者已入院接受治疗。
埃博拉——“小众”的传染病
埃博拉,本是非洲中部丛林中一条寂静的河流。上世纪70年代,这一河流流域发现的一种致命病毒以其命名,并成为死亡与恐惧的代名词。
埃博拉病毒发现至今,始终没有通过认证、确实有效的疫苗,也没有针对性疗法。过去近40年,科技飞速发展,人类却对埃博拉几乎无计可施,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种病毒的“小众”。
埃博拉固然可怕,但传播途径有限,只有直接接触患者体液才会被感染。相比之下,由空气传播的流感或由昆虫传播的黄热病等传染病更易蔓延扩散。
换言之,埃博拉是偏居一隅的传染病,发展为大规模流行病的可能性不大,对医疗体系健全的富裕国家更不足以构成威胁。
当今世界的新药研发,仍然由发达国家的少数几家制药公司说了算。开发一种新疫苗,动辄耗资数亿美元,除非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否则不会有大型药企参与其中。
即使在非洲,埃博拉疫苗的市场也不大。此前,非洲共暴发过20余次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累计达1590人。与艾滋病或肺结核等全球性传染病相比,埃博拉解药的市场微乎其微,无法刺激药企投入研发和生产。
解药研究 门槛何在?
事实上,寻找埃博拉的解药并非难如登天。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已开始相关试验,但巨额研究经费始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在欧美发达国家,即使基因病之类的罕见疾病,也有专门疗法问世。虽然患有此类疾病的人屈指可数,但只要患者肯出钱或社会保障体系愿意买单,药企投入研发何乐而不为?
埃博拉的情况正好相反,是贫穷国家里穷人生的病。无论患者还是疫情国,都无力支付埃博拉解药高昂的研发费用。
发展才是根本解药
西非埃博拉疫情说明,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发展才是战胜疾病的真正解药。
埃博拉病毒虽然致命,但只要及时筛查隔离、妥善看护,不至于大规模蔓延。这需要健全的早期预警机制、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完备的消毒防护设施,需要财力和人力的双重投入。
然而,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重灾国”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世卫组织估计,这些国家每10万人才有1名~2名医生,美国的同一比例高达245。
疫情紧急,世界各国向疫情国援助资金、药物甚至病床。世卫组织则推荐8种试验性疗法和两种试验性疫苗,尽管它们尚未经过最后的临床试验。
这仍难满足需要。联合国预计,至少需要投入6亿美元方能控制疫情。世卫组织呼吁,光有资金支持是不够的,如果非洲的整体医疗水平得不到改善,迟早会有下一次疫情暴发,还会有另一种病毒感染。
2011年数据显示,非洲54个国家中有32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投入低于世卫组织推荐的人均40美元标准。世卫组织警告,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又反过来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西非暴发疫情以来,国际社会以不同方式为非洲国家提供帮助,中国提供了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派遣了公共卫生专家。中国政府在疫情危急之际“雪中送炭”,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和非洲国家纷纷“点赞”。
控制疾病,杜绝传染,发展才是真正的解药。国际社会有义务对非洲施以援手,不仅提供对抗病毒的疫苗,更要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因为这才是抵御疾病的“终极解药”。
反思
我们不希望艾滋病的传播历史重演。艾滋病病毒最早出现在1959年一名非洲患者的血样中。如果当时举全球之力将这种“怪病”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可以避免3900万人的死亡。
今年HBO有线电视频道出品了电视电影《平常心》,催人泪下。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曾因为直到艾滋病出现四年后才正视它而给整个美国留下伤痛和败笔。本片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背景之下,讲述了第一批的纽约同性恋人群艾滋病以及HIV携带者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故事。男主角Ned Weeks作为首批被关注的艾滋病患者,向女医生Emma Brookner求助。Ned的男友Felix Turner是《纽约时报》的作者,不幸同样染病。Ned成立了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组织,并积极争取社会关注。这是一个关于战斗与抗争的故事,就像影片海报上的标语:“要想赢得一场战争,你先要发动一场战争。”
随着“鸡尾酒疗法”问世,艾滋病在发达国家得到有效控制,但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等世界最贫困的地方肆虐。
人类抗击艾滋病甚至所有疾病,不光是与病毒的斗争,也是关于医学伦理、贫富差别和社会发展的持久论战和反思。
最初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多为男同性恋,这一敏感人群受到严重歧视。我们不禁会想:如果起初是异性恋感染艾滋病,总统是否就不会四年后才正式宣布此病?
可惜一切没有“如果”。只希望历史不再重演,不再有更多生命逝去,before it’s too late。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北京诺默斯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内容由环球医学独立编写,其观点并不反映优医迈或默沙东观点,此服务由优医迈与环球医学共同提供。
如需转载,请前往用户反馈页面提交说明:https://www.uemeds.cn/personal/feedback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