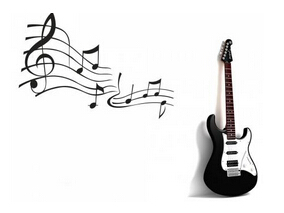说到“学霸”,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或许是带着眼镜的书呆子,在一大堆书旁边奋笔疾书。南京儿童医院的汪飞医生一定会颠覆您的观念。和他交谈后丝毫感觉不到呆木。他不但是一位称职的骨科医生,还是一位能写会唱的音乐才子,每周和志同道合之士一起玩音乐是他释放压力的主要途径。这个学霸真厉害!
博士毕业的汪飞在儿童医院骨科刚工作一年半,还是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不过在汪飞看来,这短短的一年半是他对这个职业思考最多的一年半,“工作前对于职业的感受没有这么多,从事儿童方向工作的压力远比想象的要大。”
汪飞在读博士时的研究方向是脊柱畸形,这类患儿以青少年儿童居多。由于自身对儿童比较亲近,毕业后面对众多要他的单位,汪飞最终选择了南京儿童医院。在此之前也不乏师长劝他:“儿童医院医生很累、很辛苦,和家长交流难度会比较大。”言下之意很明显,但汪飞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我在读博士期间接触过很多青少年患者,有不少都成了好朋友,到现在还有联系。”在门诊时,汪飞对待小患者就像一个大哥哥,不仅聊病情,如果时间允许还会跟他们聊生活、聊学习,甚至还会跟患儿分享学习经验。
然而,到儿童医院上班后,汪飞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儿童医院的患儿普遍年龄比较小,以5~10岁为主,几乎无法跟他们平等沟通,更多的是与家长的交流。而骨科有一半左右的患儿是因各种创伤就诊的,这些患儿的家长普遍比较焦虑,心理压力大,交流起来难度也更大,有的甚至会把压力发泄到医生身上。“当我忙着一门心思写病历时,有位家长进来找我问病情,我跟他说等我把病历写完再跟你解释,家长就很恼火,觉得医生态度太差。”在门急诊遇到的类似情况并不算少,他也曾数次反思为什么要选择到儿童医院当医生,但冷静下来后,他觉得不管选择哪个职业,前进的途中都会遇到各种困难,不如努力提高自身医术、加强学习沟通能力来得更实际。
儿童医院医生的工作环境要比想象中的更加严峻,也正是这一年半的磨练,让汪飞觉得自控能力更强了,也更会换位思考。“我本身还是很喜欢小孩的,虽然还没有孩子,但我也尽量去想想如果我是孩子的父母我会怎么做,出现这样的反应是否可以理解。”在慢慢适应儿童医院工作的同时,汪飞也希望自己能不断地学习提高,科室里很多专家都是他学习的榜样,除了继续研究脊柱畸形外,今后的工作环境还要求他不断学习其他骨骼系统畸形和创伤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儿童医院内部人士透露,汪飞还是一位音乐才子。2009年毕业季,当时在南京大学医学院上学的汪飞触景生情,写了一首《百合花开的时候》。今年在圈内发表后,产生了很不错的反响。“当时就想着留个回忆,也没想发表。”其实在医生圈里,还有很多像汪飞一样爱好音乐的,他们经常约在一起参加各种音乐活动。正是在圈内的一位大哥的鼓励和帮助,汪飞今年才鼓起勇气把献给母校的歌曲录了出来。“长期以单一的角色生活、工作会比较压抑,利用空余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多和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一起交流,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也可以促使我更好地投入工作学习。”
儿科医生紧缺是不争的事实,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让不少人不再愿意从事儿科,儿科医生转行也并不少见。前一阵沸沸扬扬的“降分”成为缓解人员匮乏的一种举措,但这种公开“降低门槛”的方式,并未得到公众的体谅,尤其是儿科专业。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项政策的出台并不奇怪,但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并没有太多方法可选。
除了儿科本身固有的特点之外,儿科在医院的地位似乎也很尴尬。郝彤介绍,因为用药量少等原因,儿科创收少,在医院中“并不受待见”,相应地,这会直接影响到科室医生的绩效收入。每天都在加班加点,收入似乎也没有多少体现。
根据报道,2010年左右,中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来为他们治疗,近两年这个比例下降到每千个儿童只有0.41位。然而全国13亿多人口中,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儿童。
“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这句在医生圈里流行多年的调侃或许也是儿科的一个写照。
专家建议,第一,从国家制度层面考虑,提出儿科医生的培养战略规划。招生的时候就动员学生读儿科,有意识地扶持儿科发展。第二,改变医生的考核制度。增加儿科医生人手,减轻儿科医生工作压力。第三,改革现下医疗收费体制,增加投入,给儿医涨工资。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
免责声明
版权所有©北京诺默斯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内容由环球医学独立编写,其观点并不反映优医迈或默沙东观点,此服务由优医迈与环球医学共同提供。
如需转载,请前往用户反馈页面提交说明:https://www.uemeds.cn/personal/feedback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 Merck & Co., Inc., Rahway, NJ, USA and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